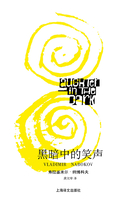
▇
西柏林,五月的一个早晨。戴白帽的人在清扫街道。谁把旧漆皮靴扔在沟里啦?麻雀在常春藤上喧闹。一辆轮胎饱满的电动牛奶车顺畅地运行着。一幢楼房的绿瓦屋顶上的阁楼窗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清晨的新鲜空气还没有适应远处车辆的喧嚣,它只是轻轻收集了各种响声,小心翼翼地携带着,好像这些声音是贵重而易碎的物品。门前花园里盛开着波斯丁香。尽管早晨寒气袭人,白色的蝴蝶却仍像在乡间花园里那样翩翩飞舞。欧比纳斯从他过夜的公寓走出来时看见了上述情景。
他隐隐感到不适。他饥饿,没刮脸也没洗澡。隔夜的衬衣贴在身上使人烦躁难耐。他觉得已经筋疲力尽——这并不奇怪。这一夜他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初次亲吻她生着汗毛的脊背时,她把两个肩胛缩拢来,同时发出愉快的低吟。这真是他一心想望的风韵,他喜欢的可不是那种天真而冷漠的小雏。先前最放肆的想像现在都能实现。在这自由自在的天地里,什么清教徒式的爱情,什么古板的规矩,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的裸体姿态自然,好像她一直就是在他梦中的海滩上漫步的那个姑娘。她在床上的体态灵活而优美,亲热一番之后,她会跳下床来,在房里踱来踱去,扭着她少女的腰肢,一边啃着晚餐剩下的干面包卷。
当电灯变成死囚牢房的黄色,窗户泛出神灵的蓝光时,她突然睡着了,好像话说到一半忽地闭嘴不语一样。他摸进浴室,可水管里只流出铁锈色的几滴水。他叹了口气,用两个指尖从澡盆里捏起一个软搭搭的丝瓜瓤,又撒手让它落了下去。他审视着那块滑溜溜的粉红色香皂,心想他一定要教会玛戈讲究卫生。他的牙齿直打颤。他穿上衣服,把鸭绒被盖在睡得正甜的玛戈身上,吻吻她温暖、蓬乱的黑发,在桌上留了个字条,就踮着脚尖走了出去。
当他步行在和煦的阳光下时,他意识到,清算自己行为罪过的时候就要到了。他又来到他和伊丽莎白一道居住了那么久的公寓;他上了电梯——八年前他和保姆、妻子就是乘着这部电梯上楼的,当时保姆抱着婴孩,妻子脸色苍白却又喜气洋洋。他回到自家门前,又看到他的学者风度的姓名牌闪着严肃的光。这时只要有一桩奇迹发生,他就会和头天夜晚的行为一刀两断,只要伊丽莎白没有看到那封信,他总能设法解释昨晚为什么没有回家——他可以半开玩笑地说,他到一个日本画家那里抽鸦片去了。那日本人到他家来吃过饭——这条理由还算说得过去。
现在不得不打开这扇门,走进去,看一看……会看见什么……还是不进去为好——一切听其自然。是否应当一溜了之?
他忽然想起,在战场上他曾强迫自己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不要把腰弓得太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厅里,听着。没有一点响动。每天早晨在这个时候,公寓里通常是嘈杂的:什么地方响着哗哗流水声;保姆大声跟伊尔玛说话;女仆在餐厅里把盆盆罐罐弄得丁当作响……现在屋子里竟鸦雀无声!伊丽莎白的雨伞立在屋角。他对着雨伞出起神来。他这么呆站着的时候,弗丽达出现在过道里。她没有系围裙,直愣愣盯了他一会,哭丧着脸说:
“啊,先生,昨晚上他们全都走了。”
“哪儿去了?”欧比纳斯没有看着她。
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讲得很快,嗓音也异乎寻常地高。她拿过他的帽子和手杖时忽然痛哭起来。
“您喝咖啡吗?”她抽泣着问。
卧室里乱糟糟的,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妻子的夜礼服摊在床上,衣柜的一个抽屉拉了出来。他已故的岳父的那帧照片也从桌上消失了。地毯的一角翻卷了起来。
欧比纳斯把地毯掀起的一角放了回去,随后轻轻地走进书房。书桌上摆着几封拆开的信。噢,就是那一封——多么孩子气的笔迹!尽是错字。德雷亚寄来的午餐请柬,真不错。雷克斯写来一封短信。牙医的账单。很好。
两小时之后,保罗来了。看得出来,他刮脸的时候一定挺粗心,丰满的面颊上交叉贴着黑胶布。
“我回来取东西,”他边走边说。
欧比纳斯跟在后边,裤兜里的钱币丁当作响。他默默地看着保罗和弗丽达整理提箱,好像他们正急着去赶火车。
“别忘了那把伞,”欧比纳斯呆呆地说。
他又跟在后边看他们收拾育儿室里的东西。保姆房里放着一只装好的旅行皮箱,他们拿走了那只箱子。
“保罗,听我说一句话,”欧比纳斯轻声说。他清咳一声,走进书房。保罗跟进去,站在窗子旁边。
“事情弄得很糟,”欧比纳斯说。
“我只想告诉你,”保罗凝望着窗外说。“伊丽莎白能挺过这场灾难就算是万幸。她……”
他泣不成声了。脸上贴的黑胶布一上一下地颤动。
“她跟丢了魂一样。你把她……你……你真是一个恶棍,十足的恶棍!”
“话说得太重了吧?”欧比纳斯竭力想笑一笑。
“真可恨!”保罗大声说,第一次转过身来看着姐夫。“你在哪儿认识她的?那个骚货怎么敢往你家里写信?”
“别发火,慢慢说,”欧比纳斯舔舔嘴唇。
“我真想揍你一顿,真想杀了你!”保罗更加提高了嗓门。
“弗丽达在外边呢,”欧比纳斯小声说。“留神她听见了。”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保罗想揪住他的衣领,他苦笑着打了一下保罗的手。
“我不愿意受人盘问,”他轻声说。“这件事很不幸。你不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吗?你瞧……”
“你撒谎!”保罗用椅子顿着地板吼道。“你这个无赖!我刚去找过她。那个小骚货,应该关进教养院。我知道你会撒谎的,你这个无赖。亏你干得出这种事!这不仅仅是过错,这简直是……”
“够了,”欧比纳斯打断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一辆卡车开了过去。窗框微微发颤。
“欧比,唉,”保罗忽然平静,忧伤地说,“谁又想得到……”
他走了出去。弗丽达在侧厅里啜泣。有人把行李提出了门。屋里又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