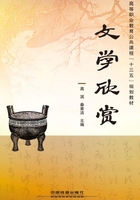
一、文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含义
文学是以语言来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家思想情感的一门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一样属于上层建筑。
文学是语言艺术,是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学的对象是人与人的生活。作家是社会的一员,他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拥有特定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他对生活的评价,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一定利益集团或文化视野与读者对话。文学通过读者接受活动,产生了社会影响,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读者层产生作用。
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人们只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一定内容的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是证明,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以抽象的概念、严格的逻辑论证来提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探索生活的真理;而文学则是以生动具体的感性形象来显现生活面貌,引导人们去体察生命的真谛。总之,用形象说话,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观点及意见,是文学的特殊功能。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人类认识世界和表达认识的方式一共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科学,靠着科学找出基本原因和基本规律,用正确的公式和抽象的字句表达出来。第二条路是艺术,人在艺术上表现基本原因和基本规律的时候,不用大众无法了解而只有专家懂得的枯燥的定义,而是用易于感受的方式,不但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最普通的人的感官与感情。正是这种特殊的认识或“掌握”客观世界的方式,决定了文学艺术必须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来描绘生活,表达主体的思想与感情。
形象是依据现实生活,经过语言艺术概括,表现在作品中具体可感,鲜明生动,并体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主要指人物形象。
任何形象都是具体的。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形象来自现实生活,是生活原型的生动再现。现实生活中的事物都是具象的,具有可感、可视的特点。因此,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必须形象地描绘生活的具体形态。不仅小说、戏剧这些叙述性作品的文学形象是具体的,而且散文、诗歌中的文学形象也是具体的。
文学形象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生动的。人们在分析艺术形象时,也往往把具体、生动联系在一起。前面列举的形象既是具体的,又是生动的。所谓形象的生动性,就是指文学描写的具体对象在生活中的运动形态。绘画和雕塑的形象固然也具体生动,但表现的是动态在一瞬间的凝固状态。而文学形象却不然,它可以描绘出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外在行动和内心状态的变化过程。因而,比之其他艺术,文学形象的生动性尤为突出。
(二)文学与生活
1.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又高于生活
文学即是人学。文学在不同时代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是为了批判,为了颂扬,为了唤醒,为了激励,为了娱乐,为了消遣,更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反观自身,认识生活,思考生活,理解生活,好好生活。
生活是指人类生存过程中的各项活动的总和,范畴较广,一般指为幸福的意义而存在。生活实际上是对人生的一种诠释,它是比生存更高层面的一种状态,也是人生的一种乐观的态度。社会生活为文学的创造提供了有利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同志认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文学创造的客体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统一的社会生活,是整体性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审美价值或审丑价值的社会生活,是作家体验过的社会生活。
2.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
生活真实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人、事、物。
对于文学艺术而言,生活真实是作为基础与源泉而存在的。尽管文学作品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抒发人们的感情,有的描写自然景物,有的描写超现实、非现实的幻想,但不管它们彼此怎样不同,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生活真实是文学的“源”,古代的作品、历史资料等是文学的“流”。文学创作只是对生活真实的艺术加工和处理。没有生活真实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艺术创作。
当然,生活真实虽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和前提而已。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真实的能动反映过程。作家必须对生活真实进行艺术的取舍、改造、提炼、虚构等创造性加工,才能使生活真实变为文学作品。就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尾曲所唱的那样:“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3.文学创作中的灵感
灵感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是指作家在偶然机遇的触发下,艺术想象高度活跃,艺术技巧超常发挥,创作进程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的心理状态。陆游《剑南诗篇·文章》中“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文学创作中的灵感现象,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突发性,二是短暂性,三是突破性。一方面,灵感基于作家长期的艺术积累和勤奋的创作劳动;另一方面,灵感的产生还要有适当的契机触发。不过灵感毕竟是一种短暂的心理现象,并不能帮助作家解决创作过程中的所有问题。灵感对于人类的启发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在睡眠中制作成了化学元素周期表,这与门捷列夫平时对化学元素的认真思考有密切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在睡眠时思想放松,反而有利于思维进一步扩散,这表明思维放松可以促使灵感的产生。科学研究需要灵感,艺术创造更离不开灵感。
著名音乐家施特劳斯有一次站在多瑙河边,望见碧波掠岸、浪花涟漪的优美景象,不知不觉地同音乐联系起来,突然来了灵感,产生了妙不可言的音乐旋律,他急忙取出笔想记录下来,却发现没带纸。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衬衣,在衣袖上及时记录了这个旋律,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不朽之作《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基础。
(三)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
文学是人的精神创造的产物,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总是带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具备某种价值。人类之所以需要它,正是因为文学对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进入社会系统之后,必然会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甚至推动着社会变革和改造。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意思是说,诗歌能起到激发人心的作用,能够帮助人们观风俗之盛衰,也能使人团结,针砭时弊。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能够给人以真理,罗马时代的贺拉斯要求文学“寓教于乐”,都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
文学对于社会来说不是消极的、被动的东西,而是积极参与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力量。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社会作用就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文学只有通过阅读,影响读者、教育读者、调节人的情绪、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来间接地对社会产生影响。文学就是用美来感染人、愉悦人、影响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状态——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发生深刻的变化。
1.文学的美悦作用
在文学欣赏过程中,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以感觉上的快适和精神上的愉悦满足。人们对作品的内容,如人物的行为、命运和种种生活情景,在感情上产生强度不一的反应,引起或优美,或丑陋,或崇高,或卑劣,或悲痛,或可笑的感觉,从而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满足。
文学描写美的事物固然能使作品具有美的品质,而描写丑的东西也可以产生审美价值。十七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塑造了一个守财奴的形象阿巴贡,他为了敛财聚宝,费尽心机,甚至六亲不认,冷酷无情。这样一个吝啬鬼却具备了审美意义,作家通过对他的讥讽、嘲弄,否定了他的丑恶行为,衬托出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所以丑一旦进入了艺术领域,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也就是通过对生活中的丑的否定,达到了对艺术美的表现。
从心理学上看,文学通过情感宣泄和补偿来调节人的情感而产生愉悦的心情。阅读文学作品时,人们得到一种审美快感,在他们各自的艺术对象中宣泄了他们平时的一些情绪,达到一种平衡感,不断提高人的境界。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剧中多次出现的“汉家基业”“俺汉家节”等一类唱词,借历史人物之口,激起人民的民族情感,鼓舞他们积极为反抗民族压迫而斗争。文学对人的精神有着重要的补偿作用,当人们某种需要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时,可以从另一种方式,即从艺术中得到补偿。也就是文学可以补偿现实的缺憾。意志薄弱者,却可以有鲁滨逊、保尔·柯察金的坚强;虽无爱情,却有罗密欧、朱丽叶的柔情。现实中不存在的也可以在文学中求补偿。
2.文学的认识作用
文学反映的对象是人的生活,文学在描写历史和现实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来创造艺术形象,因而优秀而深刻的文学总是表现了生活的内容和人生的真谛。比如人们读杜甫的“三吏”“三别”,就能了解到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许多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仿佛具体而生动地看到新婚夫妇被迫离散,老妪被迫投军,田园的荒废,官吏的无情,生活的困苦,人民的哀怨,都历历在目;一幅幅悲惨的景象,一声声哭诉的声音都在眼前。
文学的认识作用,可分为表层认识和深层认识。比如过去时代的作品使我们了解了古代人的风俗习惯、劳动情形、生活状况,使人从中获得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使读者了解到外国民族的生活情况等,都属于表层认识。只有当文学作品精细到再现当时各种社会心理和人民情绪的细微变化,政治力量或阶级关系的变动对比,使作品准确、深刻而又形象地描绘出社会发展演化的实际状况,揭示出历史过程的某些规律性,这样的作品就使人获得一种深层认识。一般文学作品只具备表层认识,只有那些优秀的、真正揭示生活真理的作品才具有深层认识。
3.文学的教育作用
文学作品总是影响人的心灵和行为,帮助人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也会产生共鸣和思索,甚至得到心灵上的震撼,从中得到启示和教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人们不仅会心中崇敬保尔·柯察金、林道静等,而且会在现实生活中学习他们、仿效他们。美国作家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讲了一个可笑的故事。苏比,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因为想去监狱过冬,便以身试法:吃饭不给钱,扰乱社会治安,当着警察的面调戏妇女……结果却屡试屡败。当苏比无奈地踱步到一座古朴教堂前时,赞美诗演奏的甜美乐声使他陶醉。他的灵魂突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一种强烈的﹑突起的冲动推动着他与厄运抗争。
文学的“初级关怀”与“终极关怀”。所谓“初级关怀”,是对人们生活情绪的放松、抚慰、宣泄,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如通俗读物。所谓“终极关怀”,则是对人们生存意义的感悟、理解、追问,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如《俄狄浦斯王》绝望的挣扎,《浮士德》顽强的探索,《哈姆雷特》沉痛的反思,《离骚》上下求索,《牡丹亭》生死之恋,《红楼梦》色空之谜等。这些作品都具备终极关怀,文学所实现的“初级关怀”也便具有了人道主义的合理价值;而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当人们的物质欲望已得到充分膨胀,渴望获得必要的感性超越和精神救赎的情况下,文学艺术则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终极关怀”的文化使命。
文学是用生动的形象来反映、说明和评价生活,因而文学教育作用并不是赤裸裸的说教能达到的,而是通过生动活泼形象潜移默化地感染、打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