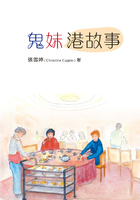
第7章 初抵香港
到1985年8月,我終於攢夠了去香港的來回機票錢。仁兩週之前就已經從法國回香港了。這不僅是我第一次去香港,還是我第一次來亞洲。我一直覺得亞洲魅力無限。這源自六歲那年我從老師那處認識到日本的習俗和節慶,我們在幼稚園的院子裏掛上紙做的彩色鯉魚,慶祝日本的男孩節。後來我還學會怎麼用筷子,不過直到十歲那年才真正算用過筷子吃飯。那是在一家叫“帝宮”的中菜館,包筷子的紙套上面印着餐館的名字和標識,我留下作記念。這家餐館在離我父母家不遠的小鎮維埃納,小鎮的亞洲人主要來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撾。但對我們西方人來說,所有亞洲人看上去似乎都一樣。
關於香港,我記得初中時看過的一本世界各國百科全書,裏面有幾張香港的照片:藍天白雲下帆船星羅棋佈的維多利亞港,摩天高樓中夾雜着古舊的建築物,還有半隱在竹棚架內還在施工的新商廈,這些照片都是西方人慣常的取景,無甚新意。我來香港除了想真正認識香港,還要去看望仁的媽媽,仁早就告訴她我是她唯一的兒子的女友。她倒是不介意仁找外國女朋友,只要不是黑人就行。我猜她是因為從來沒接觸過黑人,所以不習慣他們的黑皮膚。後來和她相處,我覺得她那麼和善,就算仁要娶個黑人回家,她也一樣會疼愛。
1985年8月5日是個很重要的日子,這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飛機。我訂的是泰國航空公司的航班,從巴黎戴高樂機場出發,我特意要求坐靠走廊的座位,因為我覺得起飛時看見窗外不斷遠離的地面會很可怕。飛機上以英文作廣播,我大半聽不懂。飛機起飛時,我一直緊緊抓着扶手,眼睛盯着放在腿上空姐送來的迎客蘭花。一直到飛機平穩飛行,空姐開始派發餐單和帶茉莉香味的濕巾時,我才鬆了口氣。飛機在曼谷作中途停留,這一程夾雜着遠行的緊張和即將見到仁的興奮,我幾乎都沒怎麼睡着,覺得有點疲倦。飛機再次起飛時我已沒先前那麼緊張了。從曼谷到香港飛行時間不長,隨着一陣劇烈的耳鳴,我聽到機長廣播飛機即將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
我早知道香港啟德機場因為建在市區,飛機降落時幾乎是從一排排居民屋頂擦邊而過,聽說乘客甚至可以看見樓裏的人們在吃飯。但因為我坐在靠走廊的座位沒機會見到這樣的景象。入境時我拿到三個月的逗留許可,然後拖着行李箱朝前走,忽然驚覺自己已身在一群亞洲人之中,不免有種陌生感。我努力尋找仁的身影,然後我看到他,站在迎接旅客的黃線之外,微笑望着我。兩週的分離,似乎已隔很久。現在,真不敢相信我已經到香港了!
一出機場我才發現香港有多麼悶熱!這樣的熱浪是我從不曾經歷的,空氣濕度很大,我瞬間覺得全身都是黏黏的,仁的眼鏡也馬上結了一層水霧。街上充斥着風乾海鮮的鹹腥味,而這個城市居然叫“香港”。我們站在排成長龍的隊伍中等的士,幸好一輛輛紅色豐田皇冠魚貫而入,我們倒也沒等太久。的士飛快行駛,穿過海底隧道,我們沒多久便到了灣仔。這裏高樓林立,我抬頭看到樓外掛着各種巨大的招牌,上面的漢字我一無所知。這些商標、廣告如一張五顏六色的天網,罩住了狹窄而錯綜的街道。
我們下車的地方是軒尼詩道和莊士敦道的交接處,也在克街和茂羅街之間,這裏便是仁的家。他家住在十三樓,一樓大堂的信箱上寫着“288-13/F”。信箱上居然沒有住客名字,這跟法國很不一樣。不過這樣其實更容易,想想這棟大樓裏姓張的人一定不止仁的家人。只是郵遞員一定得眼力很好,不然面對這幾百個密密麻麻的信箱很容易把信投錯。
仁告訴我288和13對香港人來說是幸運數字,288的粵語發音近似“易發發”,也就是容易發財,13聽起來像“實生”,意即“一定生生猛猛”。因此之後我們便稱這座公寓為“易發發大樓”。等電梯時,來了大約十個住客,有的互相聊天,他們說的話我當然不懂。電梯一到,大家都蜂擁而入,也不管是否擠到了旁邊的人。我們剛進電梯,門馬上就關了,因為有人用力地按着關門按鈕。我還以為這麼拼命按關門鍵的人一定有要緊事所以回家心切,但後來發現所有人都這麼做,我想香港人真是忙到顧不上禮儀了。
進了家門,仁首先介紹我認識他的媽媽,他們說的是粵語。他媽媽當然不會像法國人那樣以親吻和擁抱問候,她只是看着我咧嘴笑。然後仁介紹我認識他的姐妹,見面“儀式”很簡單,就是點頭或說“你好”。香港人的問候方式比起法國人內斂很多,法國人向父母道早安晚安時都會親吻他們。我離開法國那時,似乎不怎麼熟悉的人也流行見面互相親吻臉頰,男士們也如此。
仁是家中獨子,有兩個姐姐和三個妹妹。他父親六年前就過世了。兩個小妹還在上大學。他的姐妹都會講流利的英文,大姐和五妹還會說法語,這讓我倍感親切,很想融入這個多語種的家庭。不過仁的媽媽不會外語,我名字中的“r”音她也不會發,於是在她口中我的名字成了“紀詩婷”。仁讓我叫他的媽媽“媽咪”,這樣就不像“張太太”那麼生疏。媽咪有張圓臉,戴着眼鏡,一頭燙過的黑色短髮梳到左邊。她身着褲裝,上身穿印有花朵圖案的T恤。後來我注意到,她頗愛打扮,常常塗着鮮紅的指甲油,只是她很少穿裙子。她老家在廣東順德,在家裏排行第七,有一個哥哥,五個姐姐和兩個妹妹。兩個姐姐(我們叫三姨媽、四姨媽)住在澳門。除她之外,只有最小的妹妹(我們叫九姨)和她的哥哥(也就是仁的舅父)住在香港。要按照他們的排行來稱呼這些長輩,對我來說太難了,因為在法國我們不會作如此區分,比如我媽媽有三個妹妹,我爸爸有一個姐姐,我都一律叫她們“姨姨”,不會區分誰是姨媽,誰是小姨,也不用管她們誰是姑媽,誰是小姑。
我記得和仁的家人的一頓晚餐是晚上七點開始;而七點的香港,夜幕已低垂。法國的夏天,白天很長,到十點天仍亮如白晝,而香港七點天就黑了,對我來說夜晚來得太早。在法國,通常太陽落山氣溫便下降,可是在這裏,到了晚上熱度依然。我還記得那天的晚餐先是一碗棕色的熱湯,好像是蓮藕豬骨湯。湯端上來後,大家把煲湯的食材都撈出來,放在另一個碟子裏分吃。我一般不會在夏天喝熱湯,何況是味道這麼濃郁的湯,但我還是硬着頭皮喝了。那時我不會想到,自己後來竟愛上了港式湯。這是我在香港的第一個晚上,各種和法國的不同讓我有些應接不暇。
過了幾天,仁帶我去一家茶樓和他的舅父舅母一起飲茶。舅父用法語跟我說“謝謝”,“早晨”,“是的”,雖然他只會寥寥這幾個詞,但還是顯得很自豪。他還不斷重複着一句話,聽起來好像是個笑話,一開始我沒聽明白,後來才知道他是在說法語的“你好嗎”,這句話聽起來像粵語的“今晚打老虎”。吃完飯舅父送給我一隻陶瓷公雞,公雞是法國的象徵。對這位有趣又有心的舅父,我很是喜歡。
又過幾天,仁帶帶我去看望他的祖父母,兩老住在新界大埔。香港人稱祖父母為爺爺嫲嫲,不過仁按照家鄉的習慣叫他爺爺“阿公”、奶奶“阿婆”。阿公那年八十二歲,阿婆小他一歲,兩人都出生在上海,但他們的父輩都來自廣東中山。阿公阿婆共有五個孩子,也都出生在上海。仁的爸爸最年長,他1949年從上海隻身來到香港,六十年代阿公阿婆帶着長女和么女也到了香港,另外兩個女兒則一直住在上海,但他們的長女,也就是仁的二姑姐已經過世了。
阿婆個子不高,戴一副紅框大眼鏡,梳了朝右分界的齊耳短髮,頭髮已經班白,穿着中式對襟衫。她和我想像中的中國老太太一模一樣。阿公也是一頭斑白頭髮,眉毛濃密。他穿着背心短褲,腳踏布鞋。看到孫子學成歸來了,還帶着既開朗又富冒險精神的法國女友,阿公阿婆都笑得很開心。那時因為語言不通,我沒法和仁的家人交流,對此我覺得很遺憾。不過我暗下決心要學粵語,因為畢業後香港就會成為我以後的家了。我聽說有很多西方人,在香港住了很久,卻不會講粵語,這實在是我難以想像的。但後來我慢慢知道為何如此,因為粵語比我想像的難太多。
從大埔回到灣仔,更覺得灣仔擠迫熱鬧。我們的“易發發”大樓的門白天總是敞開,有個看更監察着進出大樓的人。他背後的一台電扇在夏日總是開着,給濕熱膠着的空氣帶來絲微涼意。也許是這台電扇單調的嗡嗡聲讓人昏昏欲睡,這名看更經常都看似睡眼惺忪的。在法國住宅大廈是沒有門衛的,因為人工太貴。仁他家的這座大樓有三部電梯,一部只停奇數層,一部停偶數層,還有一部停所有樓層。
仁的家有800多平方呎,這在香港算很寬敞了。家裏四間卧室,兩間小的裏面各放一張上下架牀(俗稱碌架牀),兩間大的各有一張雙人牀。因為仁是家中獨子,所以享有一整間大卧室,這是他從法國回來之前他姐姐特為他收拾出來的。
家裏廚房很小,僅擺放一個切板,一把中式菜刀,一口鍋和一個煤氣爐。而法國人的廚房通常有微波爐、食物處理機以及各種不同功能的鍋碗瓢盆,一應俱全,只是擁有這麼完善的廚房設施,卻不是每個法國人都深諳烹飪的藝術。家裏的窗戶通常都是開着的,大門外因為還有一扇防盜鐵閘,所以大門白天也開着,這樣可以增加空氣流通,讓室內不那麼悶熱。每間房子的窗戶都裝了鐵窗花,一開始我真覺得如置身監獄一般,但慢慢習慣之後反倒覺得很安心。冷氣機都嵌在窗戶上,雖說它們噪音很大,但如果沒有它們,我無法想像在香港怎麼度過無比炎熱的夏天。法國的家庭通常是不裝空調的,因為天熱的日子極少,夏天大多涼爽。
衛生間裏常看見大蟑螂,牠們喜愛潮濕的地方,也喜歡掉在地上的食物碎屑。雖然媽咪常常在牠們出沒之處噴藥,但似乎牠們還是前仆後繼地出現,因為家裏的門窗大多時間都是開着的。不過我倒是不怕這些小傢伙。
公寓外面的灣仔軒尼詩道總是車水馬龍,就算我們住在十三樓,還是能聽見樓下老式電車“叮叮”的鈴聲。家裏的窗戶正對一家加油站,即使到晚上,還是不停有的士來加油。窗戶沒有裝遮光的百葉窗,即使拉上窗簾,還是能感受到外面的萬千霓虹。香港似乎是個不眠之城,儘管樓內每個人很想睡個安穩覺。
每天清晨仁會到軒尼詩道去買一份英文報紙給我,這樣我可以知道新近情況順便練練英語。他還買回來港式包點當早餐,我們就泡仁最喜愛的普洱茶伴着吃。雖然包點也很可口,但我還是很想念牛角包和法式麵包,那時我們住的地方附近還沒有法式麵包賣。
媽咪在一家藥廠工作,每天的任務是包裝各種藥,下班之後她就回家給孩子們準備晚餐。她不讓我進廚房幫忙,說裏面太熱而且我也不會做中菜。晚餐做好之後,媽咪迅速鋪好“桌布”擺好碗筷,而桌布就是幾張舊報紙。在法國,我家開飯前會先鋪上防水桌布,然後擺上各種刀叉杯盤、一籃子麵包、一瓶白開水、鹽和胡椒,當然還有餐巾,程序複雜多了。晚餐過後,仁的姐姐洗碗,並把墊在桌上的舊報紙包好扔走。
飯後我們又坐回餐桌前打麻將,我和媽咪以及仁的兩個妹妹湊成一桌“麻將腳”,仁卻不喜歡打麻將。他小時候總是爸媽要去上廁所時就讓他上桌頂替一會。五妹用法語給我解釋規則,如果我想要別家剛剛打出的某張牌,就必須喊“碰”,同時亮出手裏與之相同的兩張牌,將這三張牌擺在面前。麻將桌上得眼明手快,但我因為剛學會總是跟不上節奏。媽咪常和親戚朋友打麻將,可能覺得我反應太慢,給我悶壞了,但她什麼也沒說。幸好我們只是玩玩,輸了不用給錢,否則我可能一文不名了。
打完麻將之後,仁會帶我出去散步。我們從家一直走到銅鑼灣。有時我也和仁的妹妹們去附近散步。每次上街她們都牽着我,好像我是小孩一樣。這讓我感動,但也覺得有些不自在。在法國,我不會和女性牽手走路,因為這樣必然招惹非議。但我理解仁的妹妹們帶着哥哥那個什麼都不懂的法國女友覺得責任重大,她們生怕我走丟了。
散步回來之後,媽咪還在看電視,不是TVB的“香港小姐”選拔賽,就是翡翠台的《歡樂今宵》。這個節目很受歡迎,是一個叫肥肥的女藝人主持的。電視裏總是歡聲笑語不斷,雖然聽不懂,我也跟着看看。
晚上仁的姐妹們把洗好的衣服晾在門廳天花板的竹竿上。她們怕我累着,這點小事他們也不讓我幫忙。大樓的住戶也可以把衣服晾在公寓外對着天井的公共梯台,這裏牽了晾衣線,不過雖然通風更好,大家還是只會在這裏曬一些不怎麼貴重的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