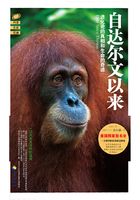
4 对达尔文理论的过早埋葬
在众多的电影《圣诞颂歌》(Christmas Carol)①版本中,其中的一个有这样的场面,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正要拜访一位要死的伙伴雅各布·马雷(Jacob Marley)时,看到一位尊贵的绅士坐在楼梯上喘息。斯克鲁奇问道:“你是医生吗?”“不,”这个人答道,“我是殡仪经办人,我与医生从事的是竞争性的行业。”知识分子残酷的世界肯定是竞争很激烈的。宣称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的死亡是引人注意的事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一直是要被埋葬的候选者。最近,汤姆·贝瑟尔(Tom Bethell)在一篇题为《达尔文的错误》(《哈泼斯》杂志,Harpers,1976年2月号)的文章中还提到“我相信,达尔文的理论正处在垮台的边缘……许多年前,甚至最热心的支持者,都在静悄悄地抛弃自然选择”。对我来说,这真是新闻,而且我虽然以作为达尔文主义者而骄傲,但我却不是自然选择最热心的捍卫者。我想起马克·吐温(Mak Twain)对预先发表的讣告所做的著名答复:“有关我死的报道太夸大其词了。”
贝瑟尔的论据对许多从事实际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是个奇特的警告。我们已经有准备看到在新材料的影响下一个理论的衰亡,但是我们不希望一个伟大而有影响的理论因系统陈述中的错误而垮台。几乎所有注重经验的科学家都比较实在。科学家愿将学院哲学作为空洞的探讨而弃之不用。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直接凭直觉来思想。贝瑟尔并没有提供足以埋葬自然选择的材料,只引用了达尔文推论中的一个错误:“达尔文犯了一个动摇他的理论的严重错误。而这个错误最近才被认识到……正是在这一点上,达尔文误入歧途。”
虽然我打算否定贝瑟尔的观点,我还是为科学家不愿认真探求论据的结构而感到惋惜。正如贝瑟尔所称,进化论的变化并不大。许多著名的理论都是由含糊的隐喻和类比联系起来的。贝瑟尔正确地发现了环绕进化论的废话。但是我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贝瑟尔看来,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已经腐坏,我却发现其中富含宝藏。
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理论的中心概念——最适者生存下来并将其优良的特性传播到整个群体中。自然选择是用斯宾塞的话“最适者生存”定义的。但这句著名术语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谁是最适者?最适者是怎样确定的?我们通常看到的关于适应度的陈述无非是“差异的生殖成功”,即比起群体中其他的竞争成员来,生殖出更多的可以生存下去的后代。哇!贝瑟尔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该大叫了。这个系统陈述只从生存的角度来定义适应度。自然选择的关键句子的含义不过是“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存”——一句空洞的同语重复。[同语重复是这样的句子,如“我父亲是个男人”,其中宾语(一个男人)不含任何信息,也不紧扣主语(我父亲)。同语重复比较容易确定,而它不是可以检验的科学陈述,即定义中陈述的句子不含可以检验的真实内容]
但是达尔文怎么能犯这么一个重大而低级的错误呢?即使对他批评最严厉的人也没有指责过他愚钝。显然,达尔文必定尝试过另外的途径来确定适应度的差异,即不仅依据生存来做适应度的标准。达尔文提出过一个独立的标准,但贝瑟尔正确地指出达尔文是按照类比建立这个标准的,这真是一个危险不可靠的策略。人们可能以为像《物种起源》这样一部革命性的书籍的第一章可能涉及的是宇宙问题和一般性的论述。但不是。第一章谈的是鸽子。达尔文用了最初50页的大部分篇幅论述动物驯化者保持优良品性的“人工选择”。他在这里确实在使用一种独立的标准。养鸽者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最适者并不是从生存的角度确定的。最适者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所需的特性。
自然选择的原则建立在与人工选择类比的正确性上。我们必须像养鸽者那样能预先确定最适者,而不是根据以后的生存来确定。但是大自然不是动物驯化者,没有预定的目的来调节生命的历史。在自然界,生存者所具备的特性必然被视为“比较进化的”;在人工选择中,在驯化开始前,“优良”的特性便已经确定了。贝瑟尔认为,后来的进化论者认识到达尔文类比的失败,并重新将“适应度”仅仅定义为生存下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动摇了达尔文中心设想的逻辑结构。大自然没有提供适应度的独立标准,所以,自然选择是同语反复。
随即,贝瑟尔提到从他的主要论据中得出的两个重要推论。首先,假如适应度指的是生存,那么自然选择怎么能成为达尔文宣称的“创造性”力量。自然选择只能告诉我们“一个特定动物类型”如何“成为数量多的”类型;利用自然选择不能解释“一种动物类型如何逐渐变成另一种类型”。为什么达尔文及其他一些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人物那样确信无意识的自然可以与驯化者有意识的选择相比。贝瑟尔认为,工业革命成功的资本主义化氛围,已经将任何变化确定为内在的进步。在自然中仅仅生存下来可能就是好的:“那么人们便开始看到,达尔文真正发现的只不过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信奉进步的倾向而已。”
我相信达尔文是对的,而贝瑟尔及其同僚是错的:独立于生存的适应度标准可以用于自然界,而且进化论者一直这样用着。但是我首先承认贝瑟尔的批评可以针对进化论的许多专业文献中、特别是将进化视为数量变化而非性质变化的抽象的数量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只是从差异生存的角度确定适应度。探讨只存在于计算机磁带中的假设群体基因A与B相对成功的抽象模型有何用处。然而,大自然是不受理论遗传学家的计算限制的。在自然界中,A优越B将通过差异生存来表达,但并不是由差异生存来确定,或至少不要这样去确定,免得让贝瑟尔等人获胜,达尔文失败。
我对达尔文的维护并不惊人、新奇,也不深刻,我只是认为达尔文以动物驯化类比自然选择是有道理的。在人工选择中,驯化者的欲念代表了群体的“环境变化”。在这样的新环境中,有些特性是优越的(它们生存下来并通过我们驯化者的挑选传播开来,但这是适应度的结果,而不是对适应度的确定)。在自然界中,达尔文式的进化也是对变化环境的反应。这里,关键在于,一定的形态、生理和行为的特性,像是设计好了的生活在新环境中,所以将是优越的。这些特性,从工程师出色设计的标准角度看,而不是从生存下来及传播的经验事实角度看,具有了适应度。多毛的哺乳类动物进化出绒毛外表之前天气已经冷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引起进化论者这么激烈的争论呢?还好,达尔文是正确的。生物在变化的环境中具有优越的构造及功能是适应度的独立标准。然而为什么有人认真地认为糟糕的构造与功能会取胜呢?是的,实际上许多人提出过。在达尔文时代,许多竞争的进化论主张最适者(具有最出色的构造与功能)必然被抛弃。曾经使用过我现在办公室的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阿尔丰斯·海亚特提出过族的生命周期观点,在当时很流行。海亚特宣称,进化的谱系像个体一样,具有青年、成熟、老年和死亡(灭绝)的周期。衰落和灭绝是预定的。正是成熟导致衰老,构造及功能尚佳的个体死去,而脆弱谱系中迟钝、松垮的生物取而代之。另外一个反进化的观点直生论提出,一定的趋向,一旦产生,就不会停止,由于构造与功能愈加成为劣势,所以必然导致灭绝。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19世纪进化论者认为,爱尔兰麋鹿的灭绝是因为角无法停止进化的增长(见文章9),所以它们死掉,碰到树干或陷入泥潭。同样,剑齿虎的死亡通常被认为是由于犬齿过长,以致这种可怜的猫科动物不能张开颌使用犬齿。
因此,并非贝瑟尔所称,生存下来的生物所具有的特性就是构造及功能更适应的。“最适者生存”并不是一个同语重复。这句话不仅仅是对进化记录的想象或理性的阐释。这句话是可以检验的。这句话胜过那种无法就生命性质的对立依据和不同态度间做出的权衡。这句话可以超越它本身字面上的局限。
如果我是对的,贝瑟尔又怎能声称:“我认为,达尔文正处在被抛弃的过程中,或许是出于对这个可敬的老绅士的尊重,所以他依然安卧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的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旁边,正在做的只是慎重而温和地使他消逝。”他提到的“牛虻”有C.H.沃丁顿(C.H.Waddington)和H.J.穆勒,好像他们是观念一致的缩影。他从未提到我们这一代著名的选择论者,例如E.O.威尔逊(E.O.Wilson)或D.詹曾(D.Janzen)。而且他引述新达尔文主义的奠基者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辛 普 森(Simpson)、迈 尔(Mayr)和 J.赫 胥 黎(J.Huxley)时,只是嘲讽他们关于自然选择是“创造力”的隐喻。(我并不是在宣称因为达尔文主义依然有声望所以才坚持它,我也是一只牛虻,相信没有批评的观念一致的确是风暴将至的信号。我仅仅是在报道,无论那是更好还是更糟,达尔文主义依然活着,而且还很兴旺,尽管贝瑟尔埋葬了它)
但是为什么自然选择被杜布赞斯基比作作曲家,被辛普森比作诗人,被迈尔比作雕刻师,以及被朱利安·赫胥黎比作芸芸众生的莎士比亚?我不想为这些比喻的挑选做辩护。但是我愿支持这种倾向,即说明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是自然选择具有创造性。就我所知,所有反达尔文理论都攻击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被视作如同刽子手一样的否定作用,是不适者的屠夫(而按照这样的非达尔文主义机制,适应的产生是由于获得性遗传或环境直接引入有利变异)。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其中宣扬的自然选择创造了适应。变异普遍存在,方向上是随机的。变异只提供原材料,是自然选择指导了进化变化的过程。自然选择保存了有利的变异,并逐渐形成适应度。事实上,就像艺术家从笔记、词汇和石头的原料中形成他们的创造,关于自然选择的隐喻并非不恰当。贝瑟尔由于没有接受独立于生存的适应度标准,所以他很难承认自然选择具有创造作用。
按照贝瑟尔的看法,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具有创造力的概念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及政治激发出的幻想。在英帝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乐观主义形成中,变化被视为内在的进步。为什么自然界中的生存不能等同于不是同语重复意义上而是更佳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更高适应度呢?
我竭力主张一个普遍性的论点,科学探讨出的“真理”通常是当时流行的社会及政治信念激发出的偏见。我曾就这个问题写过几篇文章,因为我认为通过揭示科学实践与人类所有的创造性活动相似,从而有助于揭开科学实践的神秘面纱。但是一般论点的真理,并不说明在任何特定的应用中都是正确的,而且我坚持认为贝瑟尔的应用就是一种极为错误的误用。
达尔文分别做过两件事情:他使科学界相信进化的发生,并且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作为进化的机制。我情愿承认大家都将进化等同于进步,从而使达尔文的同代人感到他的第一种观点悦耳一些。但是达尔文终其一生都未使人们信服他的第二项探讨。直到20世纪4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取得胜利。依我看,自然选择理论之所以没有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广泛接受,主要是这个理论否认在进化作用的内部存在一般的进步。自然选择是(生物)局部地适应变化环境的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没有提出更完美原则,不保证一般性的改善,简而言之,没有提供理由来认可那种赞同自然界存在固有进步的政治气氛。
达尔文独立的适应标准就是“改善的结构与功能”,但并不是当时英国人赞成的宇宙意义上的“改善”。对达尔文来说,改善只意味着“面对直接的局部环境具备更好的结构与功能”。局部环境不断变化:或冷或热,或干或湿,或成草原或成森林。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就是通过差异性地保持生物更佳的结构与功能,从而跟上环境的变化,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任何宇宙意义上看,哺乳动物的毛发都不是进步。自然选择可能产生了一种趋势,诱导我们设想更一般意义上的进步——脑容积的增加成了不同哺乳动物种群进化的标志(见文章23)。但是大的脑容在局部环境中才有用途,并不存在向着更大状态变化的内在趋向。而且达尔文还曾得意地表明,局部适应经常产生出结构与功能的“退化”,例如寄生动物解剖结构上的简单化。
如果自然选择不是进步的理论,那么它的声望便不是对贝瑟尔所说的政治见解的反映。我坚持认为,或许天真了些,自然选择理论现在有增无减的声望,必定与它成功地解释了我们所拥有的公认不太完备的关于进化的信息有关。我甚至猜想,查尔斯·达尔文还会伴随我们一些时光。
① 原著为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