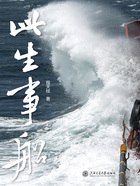
五、艰苦的造船工种
现在我国造船工业的产能、产量和订单都已位居世界第一。随着科技的进步,船舶行业也已不再是“繁重艰难”的苦活,在我求学的时代,我国船舶工业处于创业之初,称得上“十分艰难”。
有一次,学校勤工俭学,我们班里接了个活,到一个小船厂拆船。我和几位同学被分配去拆除船舱里的保温层。这保温层姜黄色,状似厚棉胎,纤维扎入皮肤如针刺。当时不知为何物,有说是石棉,有说是玻璃棉,有说是两者混合物。我们几个戴着有呼吸过滤器的面罩,穿着工作服,在舱室里整整干了一天,浑身大汗淋漓,手脚被针状纤维扎得痛痒难忍,天黑才收工。石棉和玻璃棉后来被限制应用,现在船上肯定不会用这类材料来保温隔热了。
不记得勤工俭学有没有报酬,只记得每人得了五支香烟,这是非常受欢迎的。我怀揣着这五支香烟,连夜回家。父亲烟瘾很大,但那时是困难时期,香烟限购,他的月配额早已抽完,正在难熬之时。我见他眉开眼笑接过香烟、迫不及待点燃一支,狠狠吸了一口,几乎烧了小半根。看他满足的样子,让我忘了自己辛苦的一天。
后来我们到上海船厂劳动实习,我被分配到铆工班。那时船舶焊接还属新技术,上海船厂修理的船舶不少是老旧船,是铆钉连接的。即便是新造船,舷边和甲板连接的这道重要接缝也还是铆接的。铆工是十分艰苦的技术活,且很危险。幸而我跟的师傅是位技术高超、心地善良的老工人,他未让我真正上手,只让我陪着他,递递工具,搭搭手。
我在铆工班实习一周左右,终生难忘。船停泊在码头边,要换掉锈蚀严重的外侧板,即便是三五千吨的船(现在说来是小船),要换的板也高高在上,要走上舷侧两三层木板舷梯,来到舷边跳板上工作位置。需铆上的新钢板四周已钻好三厘米左右的洞孔,和需要铆接的船体板用几个螺栓临时固定。
师傅拿锤子打击几下船体钢板,和船舱里已在工位上的互相见不着的另一位搭档师傅联系,对方也用锤子回击几下以示准备好了。随后大家各自试试气压风锤。风锤拖着长长的橡胶气管,气管另一端接着远处岸上供应压缩空气的气站。压缩空气一接通,就能驱动风锤的活塞往复运动,连动锤头冲击铆钉。
我师傅略事调整身体姿态和呼吸,对我说:“看着!”只见他右手脱下藤条安全帽,向下面示意一下;下面岸上的第三位搭档师傅拉着风箱让小炉子里的铆钉烧得正是火候,他用长夹子夹起铆钉,只听得他一声吆喝,一转身,长夹子往上一甩,一颗溅着火星的铆钉朝我们飞来,我师傅伸出帽子,潇洒一接,就兜住了一个长十四五厘米,直径三厘米左右,烧得通红发黄白色的铆钉。师傅随即用戴着隔热手套的左手抓起铆钉塞进了船板上的铆钉孔,转手端起风锤,紧压着铆钉头“哒、哒”打了两下,船舱里师傅也立即“哒、哒”两下响应,双方隔着钢板对向冲击,等到铆钉黯淡下来,铆钉已铆紧在新旧两块板的边缘上。我师傅、船舱内师傅和码头上的师傅,三个人的协调配合,时间衔接几乎毫秒不差。
才一安定,师傅一声叫喊,码头上师傅又飞来一个铆钉,里外风锤冲击声又“哒、哒、哒”响起……
看了第一颗铆钉飞来,接着、插孔、开打、打好一气呵成的过程,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如此高难度的操作,师傅们做得如此连贯轻巧,绝不逊于一流的技巧表演。待到第二个铆钉,舱内外师傅风锤同时冲击时,我才发觉打铆钉声的震耳欲聋。
风锤冲击力巨大,打在钢板上,本来就巨响,而庞大的空船舱则是个特大共鸣器,那声响想起来可以用战场上机关枪和喀秋莎火箭炮的射击声来比较……后来师傅给我一块棉花,示意我塞住耳朵,但也好不了多少。怪不得和我师傅刚见面时,我必须和他大声说话,原来耳聋已是他们的职业病。
半天下来,打了数十只铆钉。中间休息时,师傅跟我说:“反正你以后不会干我这工作,来实习见识见识。这活不好干,耳朵肯定要聋,还有在船厂里安全事故难免,随时要注意。以前有青工不听话,把手指伸进钢板洞孔里好玩,不料更高处有块钢板滑下来,齐齐把他手指切掉了。”中午我在食堂吃饭时,觉得四周突然很安静,原来耳朵在风锤打击船舱的几小时声响中,一时恢复不过来。一星期下来,听力大减,想不到从此以后真落下了后遗症,直到今天也比同龄人听力差。
第三天,师傅问我要不要先试试接铆钉。见我束手无策的样子,就说:“你跟我就一个星期,学不好的,算了,就跟跟班吧。”“再说,接不着,掉一个铆钉到水里,就是一顿饭的钱!”
我参加工作后有过三四次劳动实习,大体知道了船厂的概貌、设施、造船厂的工种和工序,知道了造船的不易。后来我到大连造船厂蹲点,边劳动边了解船厂生产经营等情况,还在广州造船厂调研,其间也安排了几天跟班劳动。自己都觉得自己缩手缩脚的样子好笑。在广船船台装配劳动时,事前没有充分准备好。气刈钢板时,火星溅出来落在我穿的尼龙袜子上,在脚面留下不少小伤疤。
劳动中,我和师傅们都合得来,感受到他们的辛苦,体会到他们干活不仅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更有一种为国家造船的负责精神和成就感。我们国家今天造船工业能占得世界第一的位置,离不开造船工人的辛勤劳动打下的基础!

1993年,毕业32年后与几位同学在大连造船新厂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