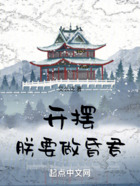
第11章 前夜
轰隆隆!
一声厚重的冬雷划破了夜空,闪耀着禁宫中的重重楼阁。
西苑。
不远处的殿檐下齐齐悬挂着一排宫灯,勾勒出一片巍峨的轮廓,其余地方都是一片静悄悄黑黢黢的旷荡。
偶尔有宫人路过时,还能听到一阵沙沙的脚步声。
李政放下了手中的木椎,起身微微活动了一下筋骨。
眼前这间的宫房,正是吕后之前答应划拨给他的殿宇。
在正式入驻之前,这里已经被空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连殿檐下悬挂牌匾的位置,都早已落满了灰尘。
如今。
李政不仅给这里挂上了匾额,还给这座宫殿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豹房。
一来,是他对明武宗朱厚照的致敬;
二来,也包含着一层“君子豹变”的蕴意。
烛光下。
李政起身,缓缓推开了一扇偏殿的木门。
这里面早就是一片狼藉。
落脚到处都是一团团揉成球状的稿纸,各类废弃的木质边角材料也丢得满地都是。
中间那张杂乱的工作台上,几张碗碟胡乱的摊开,里面是已经被吃得没剩多少的残羹冷炙。
角落里还隐隐传出一阵令人不适的涝臭。
见李政走了进来。
几个年轻的宦官匆匆行了个礼之后,便继续着手中的工作。
——他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组装着一台纺车。
这几天。
李政可以说是一门心思都扑在了这台纺车上。
从目前的组装进度来看,情况一切顺利。
在最初的计划中。
李政只是打算将现有的纺纱器具,做出一些针对性的改良。
他担心万一步子迈得太大,会容易扯到蛋。
可当尚方监把宫里的那几台手摇的纺纱工具抬过来之后,他当时就有些傻眼。
一般来说。
这皇宫中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基本上就代表了当前手工制造业的最高水准。
然而在李政超脱的视角和眼界看来,这些器具的生产效率,简直低下到令人无法想象。
在亲手拆装过一台纺纱器具之后,他大概了解了纺车的基本工作原理。
从高中课本中。
李政零零碎碎地记得,宋元时期曾有一位名叫“黄道婆”的民间手艺人,曾改良革新过一款三锭脚踏纺车。
这对当时长江流域的丝织业和棉纺织品的鼎盛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并且,这款三锭脚踏纺车在推广之后的几百年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使用,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的前夕。
仅仅只是将“手摇”的方式改成了“脚踏”,这一个微小的变动,却让生产效率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李政决定,要将这款纺车给复刻出来。
在大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的前提下。
仰赖于“木匠皇帝”扎实的设计基础和测绘能力,他没用多久就在宫墙上用木炭完成了初步的图纸设计。
接着,李政就将目光投向了“尚方监”。
这是宫内专门为帝王制造一应器具的官署,也是汇集着当世最专业的手工制造业人士。
“都来看看朕画的这张图,有谁看得懂吗?”
李政指那面宫墙发问道。
当时。
尚方监里那些朴实精业的工匠们在图样前端详了半天,支支吾吾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最后,还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宦官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回陛下,小人看得懂。”
“这墙上画的,应该是一架纺车.....”
这个小宦官似乎一眼就看懂了三锭纺车的设计理念,并且还当场提出了很多针对性的意见。
李政一听立马来了兴致,随后就对他进行盘问了一番。
结果没想到。
这一问,还给他问出了惊喜。
这位小宦官的名字,叫蔡伦。
自称是出身于铁匠世家。
不仅对各种冶炼铸造,种桑养蚕等各项生产工艺都很高的造诣,还特别擅于总结经验。
平时闲着没事的时候,也经常喜欢搞一些创造发明。
二人一拍即合。
随后,整个尚方监就在豹房里全力复刻三锭纺车。
并且还在一些细节上,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改良。
整整三天。
李政寸步未离,就连眼睛里都熬出了血丝。
而这一番沉浸,自然也让一旁魏忠贤有些摸不着头脑。
很明显。
作为一国之君,李政不是一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这宫房里将那些木料通过刨、锯、锉、磨......等一系列加工,也算不上是什么悠闲的娱乐活动。
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陛下不但对这里脏乱的环境没有半点不适,反而还一直是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
尤其是李政在木工手艺上所表现出来的精湛程度,竟然还能让尚方监的匠人们为之赞叹不绝。
这一度让他感到有些陌生。
看到李政好不容易闲了下来,魏忠贤这才连忙捧着一杯热茶跟了进来。
这些天。
他只看到尚方监的人把那堆木头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捣鼓些什么。
想要上去帮忙,却前前后后已经被嫌弃过好几次。
偏偏李政又对此事格外的看重,这给他急得是抓耳挠腮。
“陛下,这到底是在造什么宝贝啊,奴才怎么越看越糊涂了?”
“造纺车。”
魏忠贤愣了一会儿,“这模样......怎么跟太后宫里的不一样呢?”
李政抿了口茶,没好气道,“不该问的就别问,你又不懂。”
说完。
便又把茶盏递了过去。
“奴才多嘴,奴才多嘴.....”
魏忠贤脸上赔着讨好的笑容,心下却是一凛。
他眼神迅速瞥了一眼不远处正在忙碌的蔡伦,心头陡然升起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
眼见纺车的制作进展顺利,已经进入了尾声。
李政转头,又回到了豹房的主殿。
这段时间他忙得脚不着地,百官们也同样也没有闲着。
自打那次罢朝之后,朝堂上引发了一阵自发的连锁反应。
先是罢朝后的第一天,文武百官们推举秦王为首,联名上了个请罪的折子。
在奏折里,这帮人顾左右而言他,根本没有写到逼宫的事情上来,甚至还带着点道德绑架的意味。
大概意思就是说。
“陛下您赶紧息怒,秦王和百官们确实做得不对,但毕竟法不责众。”
“更何况您是天子,自然要宽宏大量的呀。”
“须知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
“陛下要是饶过我们这一回,下次就肯定不会这样了。”
“........”
李政看完之后,只是冷笑了一声。
很显然。
这根本就不是认罪的态度。
于是,他既没有批复,也没有指示,就权当没有看见。
到了第二天。
文武百官又来上朝,发现皇帝还是没来。
大伙儿又纷纷私下上了请罪的折子。
不过在那些奏折中,百官们依旧没有承认“逼宫”的罪名。
只说是受了钦天监的蛊惑,被一时迷了心窍。
李政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
再加上,他也还没完成那个【业荒于嬉】的任务。
索性,就再度没有理会。
这时候,朝臣当中有人开始对“秦王一党”心生不满了。
毕竟,他们才是这次“逼宫”事件的发起人和主谋啊!
陛下对朝臣们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事。
普天之下,有那个帝王能够容忍这样的逼迫呢?
但“燕王党”和“太后党”的人,是受了无妄之灾呀!
兵部尚书曹操也跳了出来,说陛下之所以不上朝,全是因为秦王的缘故。
要耽误了军国大事,这一切都是秦王的罪责。
这番言论,顿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三方势力开始搅到了一起,争端变得越来越大。
皇帝始终不出面。
不得已,群臣们只能去找宫里的太后求情,请她出面调解。
可吕后这时候却称病不出。
当晚还下令京城宵禁十日,并让禁军统领吕布率兵严守四宫的城门。
或许是为了平息天下悠悠之口。
又或者是为了保住那一份贤德的名声。
迫于无奈。
秦王这才在宫门外长跪不起,算是负荆请罪。
三天下来,朝堂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
宫门之外。
秦王李世民已经在这里跪了足足五个时辰。
毕竟是武将出身,他的神情依然坚毅,脸上也看不到半点颓色。
只是身后的那帮文官,却大都没有这样的韧性了。
“快,快来搭把手!”
“这儿又跪晕过去一个......”
慌乱之中。
严嵩皱着眉头,身子趋前小声地说,“秦王殿下,咱们现在的局面太被动了,您要赶紧想个办法啊!”
“西宫太后显然是在隔岸观火,曹孟德等人又在朝中落井下石,要是陛下一直不出面,难道咱们就这样一直跪下去吗?”
李世民没有应声。
正如严嵩所言,当前的形势对他十分不妙。
整个皇城已经被禁军封锁,几方势力都在明争暗斗。
虽然从决定夺位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很清楚,这是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
但如今看来,自己似乎仍然低估了这一份难度。
尤其是“名正言顺”这四个字,根本让他毫无还手之力。
朝堂上,其余党派的朝臣都将“罢朝”的罪责推到了他的头上。
除非皇帝愿意主动冰释前嫌,赦免他的罪责,不然的话,他百口莫辩。
只是,逼宫这样的大罪,巍巍皇权又怎么会轻易饶恕呢?
任何事情都有代价。
而当出头鸟的代价,则尤为惨重。
李世民知道,或许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
不然他一死,秦王府背后的势力很快就会被太后吞掉,那么朝堂就会成为西宫太后的一言堂了。
死罪或可免,活罪却难逃。
“严大人,已经别无他法了,本王只能继续跪!”李世民道。
.........
与此同时。
豹房中。
李政也在思索着接下来的对策。
他原本也没有考虑这么多。
只是想着找一个由头,完成“罢朝三天”的任务。
可朝臣们因为这件事情自行争斗了起来,局面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预想。
李政粗略地分析了一下。
自己目前要拉拢的,自然是吕后这边的势力。
毕竟,她膝下无子。
而且即便是让她掌握了朝堂上的绝大部分话语权,她也无法直接坐上皇位去发号施令,只能靠着先帝的血裔来稳固自己的权益。
李政相信,现阶段只要不急于去和太后抢班夺权,哪怕是在宫里整日沉迷酒色,自己大概率也还是能坐稳这个皇位的。
但秦王不同。
他也是先帝的血脉。
退一万步来说,他也是有继承权的。
再加上这个家伙还是个后期,还代表着朝中的新生势力,不说自己这个皇帝,就是吕后和燕王,也肯定不会任由他继续做大。
魏忠贤在一旁像是看出了李政的为难,开口道,
“陛下,依奴才看,您也不用不着怜惜秦王,奴才觉得那位曹孟德大人说的对,这逼宫乃是大罪,这可是谋反的罪名,既然太后跟陛下已经重归于好了,就是下令砍了他也不为过.......”
“.......”
李政一听这话都被气笑了。
他想起自己在当键盘侠时,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说权力看起来是来自上级,但实际上却是来自下级。
秦王可不单单只是一个亲王,他的背后还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或者说,他是一整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只有瓦解了秦王底下的根基,才能拥有真正处置他的能力。
不过。
这句浑话,倒是也给李政提了个醒。
“这么说起来,朕岂不是成了他们‘借刀杀人’的刀了?”
既然眼下还没有改变朝局的能力,那最好还是让一切先维持现状为妙。
想了想后。
李政开口道,“魏忠贤,去传旨,逼宫之事就此作罢,让秦王出宫去吧。”
“诺。”
..................
仁寿宫。
吕雉刚刚歇下,便听到了窗外的传报。
“太后,秦王已经出宫去了。”
“皇帝赦免他们了?”
“是。”
吕雉闻言又稍稍坐了起来,心道:
“看来皇帝这回是真的长进了,最起码不像之前那样意气用事.......”
接着,她又追问了一句,“皇帝还在豹房吗?”
“是。”
“还是在敲敲打打,钉那些木头?”
宫人点了点头。
“这倒是让哀家有些猜不透了......”
吕后嘴里嘟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