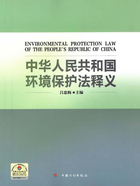
一、《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从试行法到正式法
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面临的重大生存危机。中国作为地球家族的成员,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做到“独善其身”。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遭遇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扰,我国的环境立法正是在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下、伴随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而逐渐起步并不断发展的。
(一)1949~1979年:环境立法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制定的经济复苏宏观决策一度出现政策偏差,粗放型、资源型工业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增长控制失调,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形成并积累了一些难以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1957年以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为了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实行了赶超“英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方针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先是采取“大跃进”方式,全民大办钢铁,导致“小钢铁”遍地开花,生产粗放、技术落后,没有采取任何污染控制措施,浓烟滚滚、污水横流、渣滓遍地,污染情况日益严重。乱挖滥采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植被、破坏地貌和景观、生物资源遭受劫难,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矛盾凸显。
“文革”时期,在“破除一切封、资、修”、“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的理念下,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工业上片面追求高产值带来的是资源能源大量浪费和严重环境污染;大兴“五小”工业却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导致环境质量迅速恶化;“三线”建设把许多污染严重的工厂迁进深山峡谷,导致污染向生态脆弱地区转移却又无法集中控制;不顾城市生态环境特点,推进“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运动,在文化古城建设重污染型工业,加重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战略,毁林、毁牧、围湖造田,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生态恶性循环;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滥猎乱采野生珍稀动植物,肆意破坏风景名胜,冲击自然保护区、自然与文化遗址,导致许多珍稀动物濒临灭绝、大量的自然遗产严重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迅速蔓延,中国的环境问题由发生期上升到暴发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经历了从1957~1960年、1962~1972年两个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均耕地不断减少,人均资源再度下降,迫使人们以更高的强度利用土地,不合理地开发资源。城乡建设和农村能源的短缺,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开垦草原、超载放牧,草原面积不断缩小,草地退化,沙漠化现象日益严重;粗放型经济发展更加速了矿产资源消耗。过度乃至掠夺式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使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许多物种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在国际环境保护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始起步。1972年6月,中国政府派出环境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审视了中国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情况,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工作方针;拟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3年11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卫生部联合颁布《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1978年,《宪法》中明确宣示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11条第3款)。并在1979年9月13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本节以下简称为《试行法》)。
这部法律在我国立法体系远未完备的背景下出台,十分难得。《试行法》以环境保护专门法的形式出现,是我国环境立法的起点,影响了迄今为止我国环境立法的进程:
第一,立法理念先进。《试行法》在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下制定,吸收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环境保护理念,体现了限制经济活动以保护环境的总体思路,体现了既防治环境污染又保护自然环境的“大环保理念”,并蕴含着保护环境权及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比如:《试行法》的结构上包括了“保护自然环境”(第二章)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三章)两大部分;《试行法》将立法任务确定为“为人民造成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第2条),将水资源保护目标确定为“维持水质良好状态”(第11条),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上先进的环境保护理念的影响。
第二,立法定位模糊。《试行法》在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时,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李超伯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立法说明,指出该法应该成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即主要是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因为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在审议过程中,常委们觉得不够成熟,所以采取了“原则通过”并“试行”的方式,由此埋下了环境保护法的定位之争的隐患。这部法律虽然在学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但在实际上却存在着尴尬: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试行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立法体系上不是基本法,效力偏低,其沟通作用和统领作用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试行法》的制度涉及本身多为具体制度,与其后制定的环境单行法并无明确分工,也没有体现应有的高度。
第三,立法技术不成熟。试行法制定的时代背景决定其立法技术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在法律责任制度、立法目的表述、政府管理职责、生效时间规定等方面都反映出明显不足。在内容上,也比较杂乱,比如规定了食品安全制度(第25条),直接将环境保护的工作方针(第4条)作为法律条文,用语也不够规范;等等。这些问题是在人大常委会审议时,许多意见认为这部法律只能“试行”的重要原因。
(二)1979~1989年:环境立法快速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环境问题急速恶化,环境保护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3年末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会上首次提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根据会议精神,1984年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国策[2]。另外,20世纪80年代也是我国法学和立法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由此奠基。[3]在环境保护领域也制定了一系列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法律,掀起了一次环境立法的小高潮。自此,环境立法进入了“快车道”,1983年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1984年制定《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制定《森林法》,1985年制定《草原法》,1986年制定《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渔业法》,1987年制定《水污染防治法》,1988年制定《水法》,1987年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
其实,自《试行法》实施之日起,这部法律的修订就提上了日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成立了《环境保护法(试行)》修订领导小组,并聘请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法律修订工作专班,开始进行修订。从1980年修法工作专班成立到1989年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法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但进展十分缓慢。影响修订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试行法》本身的纠结,在加快环境保护单行法制定进程的情况下,对是否有必要修改《试行法》,甚至对该法是否有必要存在,心存疑虑。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一段时期,国务院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也一直处于变动状态。我国最早于1973年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环办);1982年,国务院第一次机构改革,成立环境保护局,归属于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4年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但依旧在建设部管理范围内;1988年国务院第二次机构改革,将国家环境保护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副部级),完成了由城乡建设部下属局到独立的环境保护局的转变。
在国际上,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20世纪60到70年代的高潮后,80年代进入相对低潮期。以美国为代表,一方面,反环保的声音渐起,并在90年代初发展成为能与环境保护主义相对抗的反环保主义,“明智的利用”运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4]另一方面,政府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甚至公开宣称反环境保护,寻求各种方法消除或削弱环境管制。[5]
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本节以下简称为《环保法》),该法以试行法为基础修改而成。曲格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提出:“在执行中也发现《环保法(试行)》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有些内容也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环保法(试行)》是依据1978年宪法第11条‘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制定的。1982年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因此,环境保护的立法依据发生了变化。二是对许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没有加以确认。例如,只规定超标准排污要征收排污费,没有规定对排放某些污染物,虽然没有超标准排放,也应当征收排污费;没有规定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度;没有设专章规定法律责任,只是对惩罚作了一条笼统的规定。三是有些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例如,环保法(试行)具体地规定了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这样规定不利于深化机构改革;此外,对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限期治理,逾期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只规定要限制企业的生产规模,也不够妥当。环保法(试行)是试行法,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完善,作为正式法律施行。”[6]
纵观《环保法》的制定过程与内容,可以发现国际国内的多重因素,对于这部法律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当时的环境保护政策、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国际环保思想的发展状况。客观而言,这部法律较之于《试行法》有了重大进步:
第一,内容更加科学。其一,《环保法》坚持了大环保理念对自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加以规定,并且加入“改善”环境的规定反映了现实需求。其二,明确了环境监管体制,对于监管部门、监管职权的规定更加明确,克服了《试行法》政企不分的问题。其三,建立了环境监管的基本制度如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申报、限期治理、排污收费、防止污染转移、环境应急措施、法律责任等。其四,初步建立了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制度,加上刑法规定的环境资源犯罪规范共同构成环境法律责任体系框架。
第二,立法技术显著进步。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迅速发展的环境法学研究为制定《环保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体系性显著增强,法律责任、立法目的等的规定和表述更加合理,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也得到了较为充分考虑。
但是,《环保法》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其理念与制度一直广受诟病。
第一,经济增长观念主导。《环保法》制定时,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从政府到民间发展经济的冲动十分强烈。环境保护虽然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但并不能改变我国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从政府到民间对发展经济的热情显然高于保护环境,国际上也逐渐兴起反环保的思潮。《环保法》确立了“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目标(第4条),并被学者们总结为协调发展原则而归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7]实际上反映了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思路,与美国的“明智的利用”思潮具有一致性,其表述顺序更是要求环保顺应发展而非发展适应环保。这种平衡的思路实质上部分否定了环境保护运动所追求的环境目标的纯粹性,体现的是“发展优先”、“GDP导向”,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是基于这样的平衡思路,《环保法》删除了《试行法》中创造“适宜”环境、维持水质“良好”等提法,反映了环境目标的倒退。
第二,立法定位问题仍未解决。与《试行法》一样,《环保法》虽然在学界依然被认为是环境保护基本法,[8]但否定观点仍然存在,[9]与对《试行法》相同的质疑同样存在,其在立法效力层次、内容的统领性上并无根本改观,“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未达到基本法的要求”[10],政府官员也认为其基本法地位不突出[11]。
第三,部门立法、部分立法倾向明显。部门立法是我国立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不足之一,其问题不在于部门参与立法,而在于“行政机关借助于立法的方式使部门利益‘合法化’”[12],《环保法》也具有明显的部门立法倾向,甚至被直指为“为环保局立法”。这一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确定的环境保护任务有关,也与环境保护局刚从建设部门独立需要显示自身存在有关。但客观上使旧法表现出“为城市立法、为工业立法”、“偏重污染防治立法”的特征,从而为我国环境保护整体上相对忽视农村和农业、轻视资源保护,市场机制与公众参与严重不足埋下了伏笔。
第四,末端治理特征明显。“为污染立法”思维主导,主要制度安排集中于污染控制,生态保护与预防原则基本没有得到体现。理念的疏漏与重要制度的缺失,导致科学的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形成,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拘束力和强制力,这是造成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的原因之一。